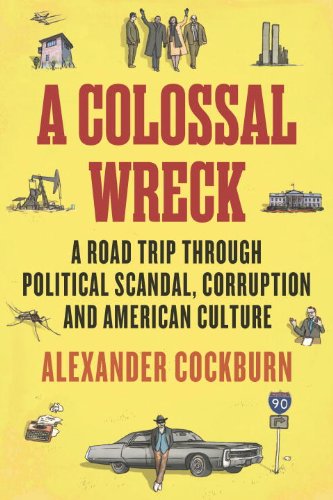◄►◄❌►▲ ▼▲▼ • B下一个新评论下一个新回复了解更多
遇到麻烦时,前往奥斯威辛集中营,最好是在埃利·威塞尔 (Elie Wiesel) 的陪伴下。 至少在犹太教-基督教的道德影响范围内,它与当今可用的角色参考一样万无一失。 人们很容易理解为什么奥普拉·温弗瑞和她的顾问将与威塞尔一起的奥斯威辛远足视为治愈奥普拉读书俱乐部所受创伤的万无一失的解毒剂,但事实证明詹姆斯·弗雷伪造了他自己所谓的自传体的重要内容。道德重生的传奇,一百万个小碎片。
弗雷(Frey)的那本令人讨厌的书于2003年出版,迅速成为了一个受人欢迎的经典。 (2004年夏天,一位年轻的亲戚向他提供了这份礼物,大概是为了帮助他恢复精神,但是翻阅了几页书后,却以不是他的这种事为由而将其退还了。)温弗瑞(Winfrey)在2005年XNUMX月为她的读书俱乐部选择了它,并迅速升至畅销书榜首。
7年2006月11日,吸烟枪网站发布了文件,显示弗雷捏造了许多关于自己的事实,包括犯罪记录,这对弗雷来说是天上掉下来的事。 后来有charges窃的指控。 XNUMX月XNUMX日,弗雷(Frey)遇到了由拉里·金(Larry King)审判的善良手套,奥普拉(Oprah)邀请她参加本月精选。 她说,重要的不是弗雷的书是否是真实的(原教旨主义者对圣经的主张),而是它作为治疗工具的价值(现代英国国教在《好书》上的立场)。
但是,到目前为止,美国的每位专栏作家和书籍页面编辑都在将真相或虚构问题扑朔迷离。 奥普拉打开弗雷。 在26月XNUMX日的演出中,他紧紧抓住绳索,提供借口说,驱使他喝酒和吸毒的“恶魔”也驱使他声称,他所写的关于自己的一切都是真实的。 包括兰登书屋(Random House)在内的出版商已经从他身上获得了数百万美元的收益,但当他最初将其作为“小说小说”提供时,却拒绝了这本书。 奥普拉无视了这一点。
“说这一切都是真的”是恶魔经常在作者耳边低语的一句话。 问 TE 劳伦斯。 德拉的贝伊真的强奸了他吗? 劳伦斯在《智慧七柱》中热切自虐的回忆段落中暗示了这一点。 劳伦斯关于英国在美索不达米亚对奥斯曼帝国的阴谋的描述中的这一冒险和其他冒险在 1920 年代初期得到了牛津相当于奥普拉读书俱乐部的欣喜若狂的钦佩,当时劳伦斯将 350,000 字的“回忆录”私下印刷和流通. 他在 1919 年写了一个早期版本,但声称这是在他从伦敦到牛津的途中在雷丁换乘火车时被盗的。 (阅读肯定是“完成的手稿”和博士论文被盗和丢失的地方——“我没有复印!”——比世界上任何一个火车站都多。)
半个世纪后,伦敦《星期日泰晤士报》的科林·辛普森和菲利普·奈特利想到了向所谓的强奸犯询问他的故事。 他们匆匆赶往土耳其,追踪了贝伊退休的小镇,到达他的家后才知道他不久前去世了。 亲戚告诉英国记者,贝伊一家不会找到劳伦斯开胃的猎物。 土耳其人是一位著名的好色之徒,在美索不达米亚时,他在去大马士革的旅行中总是因与妓女的勾结而获得掌声。
想到奥普拉(Oprah)烧烤劳伦斯(Lawrence)关于他的主张,这很有趣,他最近在烟枪上露面,告诉他她感到“确实受骗”,但“更重要的是,我感到你背叛了数百万相信你的东方受虐狂”。
但是,在被奥普拉图书俱乐部的新选秀埃利·维塞尔之夜(Elie Wiesel's Night)取代之前,弗雷几乎没有从 Amazon.com 畅销书的杰出地位中被淘汰出局,他有幸在奥普拉的这个令人担忧的时刻看到再版。文学事务。 与夜间选择同时出现的消息是奥普拉温弗瑞和埃利威塞尔很快将一起访问奥斯威辛,从这个有利位置奥普拉和阴郁的威塞尔在她身边,可以向她的 ABC-TV 观众强调有真相也有虚构,奥斯威辛是最凄凉和最可怕的历史真相,黑夜是真实的叙述,而威塞尔是真实见证的人类化身。
这里的问题是,在其中心、最关键的场景中,《夜》在历史上并不是真实的,至少另外两集几乎可以肯定是虚构的。 下面,我引用了最近几周集中营幸存者 Eli Pfefferkorn 与 Wiesel 合作多年的观点。 也是劳尔·希尔伯格的作品。 希尔伯格是纳粹大屠杀的世界权威。 耶鲁大学出版社最近重新发行了他的经典三卷本研究《欧洲犹太人的毁灭》的扩展版本。 威塞尔亲自聘请希尔伯格担任美国大屠杀委员会的历史专家。
Pfefferkorn 说,如果历史的绝对真实性是标准,那么 Night 就不能胜任。 威塞尔编造了一些事情,他的许多后来的批评者都认为他的作案手法并非不典型:巧妙地把握住对他的未来很重要的人会想听什么,同样,也不想听什么。
成为《夜》的这本书原本是一个更长的记述,于 1956 年以意第绪语出版,标题为 Un di Velt Hot Geshvign(世界保持沉默)。 当时威塞尔住在巴黎。 到 1958 年,他已将他的书从意第绪语翻译成法语,并于同年以 La Nuit 的标题出版。 Wiesel 说,Editions de Minuit 的主编 Jerome Lindon 严重缩短了它的长度。 1960 年,Hill & Wang 出版了英文译本《Night》。 2006 年版的 Night 由 Wiesel 的妻子 Marion 翻译自 1958 年的法文版,在介绍中,Wiesel 说他“能够纠正和修改一些重要的细节”。
在 17 月 1960 日的《纽约时报》上,角谷美智子用她一贯的沉闷散文写道,她一贯厌恶任何非常规的想法,“先生。 弗雷对真相的修饰,他傲慢的断言“回忆录的作者正在散播一个主观的故事”,他对人们如何记住过去的漫不经心的态度——所有这些都与将记忆作为一种神圣的行为的理解形成了令人震惊的对比。在奥普拉温弗瑞为她的读书俱乐部选择的新选择中,昨天宣布:夜,埃利威塞尔对他在奥斯威辛和布痕瓦尔德的经历的毁灭性描述。”
Amazon.com 很快就收到了消息。 该网站一直将新版 Night 归类为“小说和文学”,但根据角谷的“作为神圣行为的记忆”或威塞尔出版商的电话的明确要求,匆忙将其切换为“传记和回忆录”。 几小时内,它就登上了亚马逊畅销书排行榜的第 3 位。 同一天晚上,也就是 17 月 XNUMX 日,夜在 BarnesandNoble.com 上的“传记”和“小说”畅销书排行榜上名列前茅。
尽管如此,在接下来的几天里,《犹太前锋》和《纽约时报》上都有文章,还有一篇关于 NPR 的文章,称《夜》不应该被视为未经修饰的纪录片。 在 20 月 1996 日发表的一篇题为“六百万小碎片?”具有挑战性的文章中,约书亚·科恩提醒转发的读者,1956 年,加利福尼亚州伯克利研究生神学联盟的犹太研究教授内奥米·塞德曼 (Naomi Seidman) 比较了 XNUMX 年的原始版本。该书的意第绪语版本以及随后经过彻底编辑的翻译。
“根据 Seidman 发表在学术期刊《犹太社会研究》上的描述”,科恩写道,“威塞尔大幅改写了不同版本之间的作品——这表明意第绪语原版的刺耳和报复性语气更像是一种大陆的、充满焦虑的存在主义。适合 Wiesel 作为文化和良心大使的新兴角色。 最重要的是,塞德曼写道,威塞尔在后来的版本中修改了几个事实,在某些情况下提供了与早期版本相冲突的关键时刻的描述。 (例如,在法语中,从布痕瓦尔德(Buchenwald)中解放出来的年轻威塞尔正在医院休养;他照镜子并写道,他看到一具尸体正盯着他看。在早期的意第绪语中,威塞尔认为看到他的倒影,他砸碎了镜子,然后昏倒了,之后‘我的健康状况开始好转。’)”
也就是说,科恩强调说,“一方面,弗雷似乎为了满足自我和市场需求而伪造了他的生活事实,而威塞尔的自由似乎更像是重新考虑,他的过程与其说是解释,不如说是修改。 阅读之夜,伴随着对大屠杀的研究,人们邂逅了大屠杀思想的诞生——历史的未来。 在这两个版本中,这本书的目的不是要讲述大屠杀的不可否认性,而是要讲述一个无可否认地从恐怖中走出来的人。”
这种对威塞尔及其作品的崇敬语气是惯常的。 人们大多以一种在法国大教堂里互相阅读指南的英国游客沉默的敬畏来写他和他的作品。 在 1 月 1972 日的《犹太新闻》中,安德鲁·西洛·卡罗尔 (Andrew Silow Carroll) 有点活泼。 他引用威塞尔的话向《纽约时报》宣称《夜》“根本不是小说。 我描述的所有人都和我在一起。 如果有人提到它是一部小说,我会愤怒地反对。” 然而,Silow Carroll 继续说道,“过去,Wiesel 在这方面没有帮助。 XNUMX 年,Hill & Wang 将《夜》与另外两本书《黎明》和《意外》一起打包,Wiesel 明确将其确定为小说。 该系列的封面将作品称为“Elie Wiesel 的三个故事”。 在同一卷的后续版本中,威塞尔将所有三本书都称为“叙事”,尽管他称夜为“证词”,另外两本书为“评论”。
正如诺曼·芬克尔斯坦 (Norman Finkelstein) 的著作《哥德哈根命题和历史真相》(The Goldhagen Thesis and Historical Truth) 所挖掘的那样,威塞尔对自传真理的放松态度有一些相当可笑的例子。 威塞尔是戈德哈根的主要支持者之一。 在他 1995 年的回忆录中,所有河流都奔向大海,威塞尔写道,18 岁时,刚从奥斯威辛集中营解放出来,“我读了《纯粹理性批判》,不要笑! 在意第绪语中。” 芬克尔斯坦评论道:“撇开 Wiesel 承认当时‘我对意第绪语语法完全一无所知’,《纯粹理性批判》从未被翻译成意第绪语。” 想象一下,弗雷会因为这种空洞的吹嘘而遭受的撕裂。
虽然现在销量猛增,但我不知道有多少人会阅读 Night now,除了购买新版本作为对奥普拉和大屠杀幸存者的声援。 无需文学批评背景就可以看出,《夜》被巧妙地塑造成一种关于父子关系的象征性叙事(短书中有四幅这样的肖像),最重要的是,基督教上帝之间的关系(父)和他的儿子。 这种风格似乎受到阿尔伯特加缪的影响,尤其是 L'Etranger。 加缪于 1957 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是有史以来最年轻的获奖者之一。 在这段时间里,威塞尔正在将他的意第绪语叙事改写为更加简洁的加缪式作品,并带有加缪式标题。
作为奥斯威辛和布痕瓦尔德集中营内囚犯、死难者和幸存者经历的历史见证,有远比《夜》更好的书,从普里莫·莱维 (Primo Levi) 的著作开始,或已故的埃拉·林根斯-莱纳 (Ella Lingens-Reiner) 对奥斯威辛集中营的非凡回忆录,恐惧的囚徒,出版于 1948 年。夜的焦点非常狭窄,主要是主角埃利泽和他的父亲。 人们惊讶地得知,虽然 Wiesel 的妹妹 Tzipora 死在了集中营中,但另外两个姐妹却幸存了下来。 在新版本中,Wiesel 没有提及它们。
Night 当然不包含 Levi 或 Lingens-Reiner 提供的任何背景信息,或者最近由密歇根州立大学犹太研究教授 Kenneth Waltzer 提供的内容,他正在写一本名为《布痕瓦尔德儿童营救》的书,他的有趣的来信是XNUMX 月底发表在 Forward 上:
“20 月 XNUMX 日关于奥普拉·温弗瑞为她的读书俱乐部选择埃利·维塞尔之夜的文章很重要('六百万小件?')。 任何回忆录都是由目的和观众塑造的重建,而不是直接的记忆陈述——甚至威塞尔之夜也不例外。
“夜晚主要关注奥斯威辛和布痕瓦尔德的父子关系。 当威塞尔于 1945 年 1945 月在布痕瓦尔德失去父亲时,他陷入了无精打采和迷雾中,直到解放后才从这种迷雾中走出来。 他在夜间只回忆了集中营可怕的最后几天,即 XNUMX 年 XNUMX 月,当时纳粹试图疏散犹太囚犯,然后是所有囚犯。
韦塞尔记录了他与父亲的关系,上帝的同在以及他自己的生存及其意义。 他没有描述最后几个月他所处的社会环境。 军营,他在营地中的位置,与其他人(其他囚犯,犹太人和男孩)的关系仍然模糊。
“《夜》中省略的是,作为拯救青年战略的一部分,这名 16 岁的少年被安置在地下秘密建造的特殊营房中。 Block 66 位于疾病肆虐的小营地的最深处,在纳粹党卫军正常的视线之外。 它由捷克共产党人安东尼·卡利纳和他的副手、波兰犹太共产党人古斯塔夫·席勒监督。
“席勒在《黑夜》中短暂出现,是一个粗鲁的父亲形象和导师,尤其是对波兰犹太男孩和许多捷克犹太男孩而言; 但匈牙利和罗马尼亚的犹太男孩,尤其是宗教男孩,包括威塞尔,不太喜欢甚至害怕他。 他在夜中作为一个遥远的人物出现,手持警棍。
“ 1945年600月以后,地下集中了所有可能适合这个无窗军营的儿童和青年,共有11多名。 年幼的儿童在其他地方受到保护。 1945年900月21,000日,美国第三军到达时,在剩下的XNUMX名囚犯中发现了XNUMX多名儿童和青年。
“自那时起,Wiesel承认了地下秘密组织所扮演的角色,但没有在夜晚参加。 军营成员回忆说,他们被保护免受工作和获得额外的食物的侵害。 他们回想起导师为提高视野而付出的努力。 他们还记得在最后的日子里卡琳娜或席勒的英勇干预,以保护他们。
“即使那样,许多男孩还是在大门口排队,要在10月XNUMX日被引出。但是,美国飞机飞过头顶,警报声响起,警卫跑了,与他们同在的卡琳娜命令这些男孩回到营房。 第二天,当美国第三军部队突破铁丝网围栏时,他们仍在营房中。
“威塞尔之夜是关于变得孤独。 但威塞尔也是数百名儿童和青年之一,他们在集中营内进行有目的的营救工作。”
Forward 稍微修剪了 Waltzer 的贡献,从一篇文章到一封信。 在他亲切提供的更完整的版本中,Waltzer 教授写了他的最后一段如下:
“在《黑夜》中,威塞尔写到解放后在镜子里看到自己,看到一具尸体在回望他。 但解放后拍摄的另一张照片显示,维塞尔走出营地,左四,在一群年轻人中间,一群人昂首阔步,一群人由帮助拯救他们的囚犯引导。”
Waltzer 的文字随附一张照片,作者是纽约 Great Neck 的 Jack Werber,正好说明了这一点。 和其他人一样,年轻的威塞尔的头很高。 但是,这个人类团结胜利的寓言与威塞尔在意第绪语卷中用法语重写的寓言完全相反。 在 1950 年代后期,一个像 Wiesel 一样敏锐地调整到政治表盘上有用频率的人可能不会认为详细讨论共产党人在死亡集中营中的英雄作用是有益的。 近年来更是如此,当威塞尔最着名的时刻出现在与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进行和蔼可亲的道德咨询会议时(他想假装党卫军应该被回顾性地原谅,因为毕竟,他们不是共产主义者与大撒旦战斗)和乔治·布什,威塞尔敦促对伊拉克的战争是必要的道德行为,宣称“世界面临类似于 1938 年的道德危机”,“选择很简单”。
这不是第一次轰炸引起了伟大的道德准则支持者的积极认可。 1999年,北约炸弹降落在南斯拉夫,炸毁了火车和公共汽车上的平民,并炸死了他们广播工作室的新闻记者,维塞尔在CNN的拉里·金现场直播中受到沃尔夫·布利泽特的质疑。 宣布一个政府对另一个政府是狡猾的:“我认为(轰炸)必须完成,因为所有其他选择都已被研究。” 从道德上讲,这头秃子使维塞尔与红衣主教斯佩尔曼(Cardinal Spellman)相提并论,祝福B-52战斗机开始向越南时代的儿童投放凝固汽油弹。
(对于 Night 的优点的绝对不敬的评估 10 年 2006 月 XNUMX 日,Candian 电视观众能够在 XNUMX 月观看和聆听 Harper 杂志的前编辑 Lewis Lapham,
应渥太华大学研究生协会的邀请,在渥太华大学发表演讲。 Lapham 的演讲题为“研究的政治化”,在接下来的几天里多次在加拿大议会电视频道 C-PAC 上播放。 在讲座结束后的问答环节中,针对教育质量下降的问题,拉帕姆回答道:
“我已经有了三个孩子。 我最小的现在 25 岁,最大的 32 岁。他们都接受了非常高端的美国教育,包括中学和大学。 他们在英语课程中提供的书籍教学大纲很糟糕。 我的意思是,这些书都是小册子
“人们对奥普拉·温弗瑞和詹姆斯·弗雷的书大惊小怪,她现在要上 [她的电视节目] 艾莉·威塞尔之夜。 这真的是我读过的最糟糕的书之一,我不得不给我的三个孩子读了三遍; 而且是垃圾。 但在美国大学里,这种垃圾已经成为一种非常规矩的东西。 这是宣传
海报。 我的意思是说,有了孩子们可以阅读的那种书,这将使他们永远关闭书本。 难怪! 因为它们被赋予了大片。 而且,当然,最大的主题是受害者学。”)
Wiesel常年引人入胜的事情之一是,他的触角对于合适的听众具有超自然的敏感性,他对什么可以说“玩”对他有用的感觉。 这通过Eli Pfefferkorn将我们带到了Francois Mauriac。
这些天,现年77岁的Eli Pfefferkorn居住在多伦多。 一个人,通过几次电话交谈的证据,具有机敏的情报和魅力,他也是集中营的幸存者。 他最初来自波兰,在迈达涅克度过了七个星期,然后在三个劳教所度过,然后在布痕瓦尔德,然后在伦斯道夫。 战争快结束时,他忍受了前往摩拉维亚特雷西恩施塔特(Theresienstadt)的死亡大游行,幸存的犯人于8年1945月13日被红军解放。 ,当家人即将被驱逐出境时,她从她的手上松开了手,并告诉这名XNUMX岁的男孩争先恐后。
Pfefferkorn最终来到美国,任教并与Wiesel合作研究了大屠杀博物馆的概念设计。 曾经是一位不挑剔的仰慕者,他对Wiesel的当前估计并不令人满意,他在准备提交给出版商的一篇引人入胜的手稿中详尽阐述了自己的观点。 他很友善,给我发了一些章节。 普费弗尔科恩绝不会在维瑟尔看来是他真正的成就的短途短片。他说:“他已经成为死者的颂歌者,但他并没有对幸存者的错误举手表示反对,其中有35%低于美国的贫困线。”
在 Pfefferkorn 的回忆录中,有一些尖锐的段落涉及 Wiesel 在大屠杀博物馆设计的阴暗斗争中的机会主义和背叛,尤其是他对 1986 年获得的诺贝尔和平奖的巧妙追求。“Wiesel,Pfefferkorn 问,“曾经因为他作为记者的工作而获得过这个奖项吗?” Pfefferkorn 回答了他的问题,“这很难想象。 不。威塞尔之所以获奖,是因为他将自己提升为幸存者的代言人。 他自称是‘和平传教士’的荒谬说法与此无关。”
然后,一旦他获得了如此激烈的追求,维塞尔便逐渐地,但始终如一地让普费弗功强调“将自己与幸存者疏远了”。
在《夜》中,Pfefferkorn 分离出一些情节,在这些情节中,他提出了一个令人信服的案例,即 Wiesel 抛弃了真相而支持虚构。 我在这里引用的两个是一个男孩在死亡行军中拉小提琴,第二个是 Night 最著名的场景之一,三个囚犯被绞死。
在第一集中,Pfefferkorn写道:
“'小提琴情节'的故事发生在1945年XNUMX月从奥斯威辛集中营到布痕瓦尔德(Buchenwald)的行军中,在格莱维兹(Gleiwitz)仅有一小段空地。在党卫队后卫的残酷推动下,随行人员被枪击并推向边路。 囚犯的柱子在结冰的温度中拖着自己经过积雪覆盖的道路约五十公里后,抵达了格莱维茨。 抵达后,他们立即被放进了谷仓。 排干了水,他们跌倒在地上-死者,垂死的人和部分生活的人彼此堆叠。
“在被压碎的人类堆中,朱丽叶抱着小提琴,从奥斯威辛集中营到格莱维茨,他一直随身携带。 Eliezer偶然发现了Juliek,“……华沙的男孩在Buna乐队中演出……'你感觉如何,Juliek?” 我要问的是,他还活着,而不是知道答案,而是问他会说什么。 “好吧,Eliezer……我没事了……几乎没有空气……疲惫不堪。 我的脚肿了。 休息很好,但是我的小提琴……”
“囚犯埃利泽(Eliezer)纳闷,'这里的小提琴有什么用?' 回忆录作家维塞尔(Wiesel)认为没有必要回答这个问题。 我认为,这样的答案应该引起读者的兴趣,因为如果维塞尔提供答案,那么故事的准确性就会像西奈沙漠中的晨雾一样消散。 在行军死亡之行的过程中保持小提琴的握持是极不可能的。 但是,在人类残骸中拉小提琴会拉动想像力并质疑记忆。 朱丽叶(Juliek)在死亡旅程中是如何抓住小提琴的? 当食物和饮料被剥夺时,当每一步都顽固地拒绝跟随下一步时,朱丽叶如何设法用麻木的手指抓住小提琴,更不用说演奏贝多芬了? 党卫队的陪同人员会让他保留吗? (此外,作为爱尔兰读者,这篇文章的草稿对我说:“作为一名职业音乐家,他演奏了40多年的各种弦乐器,包括小提琴,吉他,班卓琴和曼陀林,小提琴琴弦如何在严寒和长时间的行军中生存下来?也许这是一个小问题,但非常不可能,尤其是自1945年以来,它们不是现代琴弦。”
Pfefferkorn 继续说道:“从这个世界肛门,突然听到贝多芬协奏曲的旋律,在尸体中飘荡,垂死的呻吟,死者的恶臭。 Eliezer 从未听过如此纯净的声音。 '在这样的寂静中。 天漆黑一片。 我只能听到小提琴的声音,就好像朱利克的灵魂就是弓。 他在玩自己的生活。 整个人生都在他的弦上滑行——他失去的希望,他被烧焦的过去,他的未来。 他打球,因为他再也不会打球了。 这个强大而感人的场景,庆祝人类精神战胜磨削的党卫军机器,正是英雄小说的组成部分。 但这是真实记录的回忆录吗? 显然,威塞尔在前往巴西的船上所写的公认回忆录只是他创造性想象力所见的经历的回忆。 然而,从朱利克的小提琴中传出的忧郁旋律是威塞尔和他的弟子在三十年的时间里精心编排的神话的第一部曲子。”
《夜》中的一个主要场景是对布纳工作营中三名囚犯的处决,这一场景对这本书在西方的成功以及它对从弗朗索瓦·莫里亚克开始的许多基督徒的影响做出了巨大贡献。 正如 Pfefferkorn 所写,“基督教神学家对 Wiesel 现象的迷恋必须追溯到 16 岁的 Eliezer 在奥斯维辛目睹的一次绞刑。”
在事件中,两名成人和一名小男孩被带到绞刑架上。 小男孩拒绝背叛参与破坏行为的狱友; 为了保护狱友,男孩愿意付出生命的代价。 每个人都爬到他的椅子上,他的脖子滑入绳索的套索。 1960年英文版《夜》中的场景如下:
“三名受害者一起坐在椅子上。 三个颈部同时插入套索中。 “自由万岁!” 大人哭了。 但是孩子却保持沉默。
“‘上帝在哪里? 他在哪里?' 我身后有人问道。 在营地首领的示意下,三把椅子倾倒了。 整个营地一片寂静。 在地平线上,太阳正在落山。
“'裸露你的脑袋!' 营长喊道。 他的声音沙哑。 我们哭了。 “捂住你的头!” 然后游行过去开始了。 两个大人已经不在人世了。 他们的舌头肿了起来,有点发青。 但是第三根绳子还在动。 这么轻,孩子还活着…… 他在那里呆了半个多小时,在生死之间挣扎,在我们的眼皮底下慢慢痛苦地死去。 我们不得不正视他的脸。 当我从他面前经过时,他还活着。 他的舌头还是红的,他的眼睛还没有呆滞。 在我身后,我听到同一个人问道:“上帝现在在哪里?” 我听到内心有一个声音回答他:‘他在哪里? 他在这里——他被吊在这里的绞刑架上”
毫不奇怪,由于与耶稣被钉十字架有许多相似之处,以图形描述的悬挂场景被刻入了基督教神学家的想象力。
现在,在撰写回忆录《夜之夜》时,威塞尔有理由代表一家以色列报纸访问并采访天主教作家和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弗朗索瓦·莫里亚克。 他们相处得很好。 然后威塞尔给了他《夜之夜》的手稿。 莫里亚克在书中找到了他自己对死亡集中营中的大规模屠杀,尤其是儿童屠杀的描述的痛苦的答案。
用 Pfefferkorn 的话说,Mauriac 立即确定,“受难与 Wiesel 对小男孩上吊的描述之间有相似之处。 在回答威塞尔对上帝的仁慈和人性的质疑时,莫里亚克在他的《黑夜》前言中写道:“而我,相信上帝就是爱,我能给我年轻的提问者什么答案,他的黑眼睛仍然反射着有一天出现在被吊死的孩子脸上的天使般的悲伤? 我跟他说了什么? 我有没有提到另一个以色列人,他的兄弟,他可能与他相似——被钉十字架的人,他的十字架征服了世界?'”
Pfefferkorn继续:
“悬吊在绳子上的吊死孩子反映在以利以谢的眼中,其形象类似于被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 因此,毛里阿奇一口气绘制了三幅画,使人联想到中世纪的绘画,使年轻的以利以谢成为连接西方文明史上两个分水岭事件的纽带,即被钉十字架和大屠杀。 莫里亚克毫无疑问地以他对奥斯威辛集中营的基督教学解释。 1960年,他出版了基督传记,题为“人子”,献给“被钉在十字架上的犹太孩子,代表许多其他人的EW”。
“毛里阿克解释说,在接受维塞尔的采访中,他如此有力地吸引了年轻的以色列人:'看起来,好像拉撒路从死里复活了,但仍然是他所迷路的囚徒,在绊脚石中绊倒了。可耻的尸体。” Wiesel在集中营尸体的背景下痛苦地吟着举止,启发了一代基督教神学家,将Wiesel视为后来的拉撒路(Lazarus)。
“这是一种高度推测性的建议,即从他的写作开始,维塞尔便有意识地努力将自己作为基督拉撒路人物的复合体呈现给基督教世界。 但是,一旦神话故事的种子在毛里阿克的煽动下播种在巴黎,并扎根在基督教美国的土地上,维塞尔便尽了自己的力量来鼓励“拉撒路从死者复活中复活”。 但是维瑟尔所做的更多的是手势而不是举止,沉默而不是话语,间接而不是直接陈述。 沉默寡言,沉默寡言,隐秘是他的优点。 尽管机智的情报使模棱两可,这会使许多专业外交官羡慕不已。”
在6年1994月XNUMX日给大卫·赫希(David Hirsch)的信中,阿尔弗雷德·卡赞(Alfred Kazin)写道,在他们建立友谊之初,“我非常喜欢他[Wiesel],由于他在奥斯威辛集中营的痛苦,我对他感到敬畏。” 但是同时,“……这是不可能的,当他详细介绍他在纳粹统治下的经历时,不可能错过他是个神秘主义者的事实”。
Zygfryd Halbereich是一位直接观察Wiesel所描述的悬空景象的人,他于19年1973月XNUMX日在奥斯威辛州立博物馆作证。Halbereich的证词是事实,明晰和直接的。 他与三名犯人相识,并知道他们的逃生计划。
普费弗科恩写道:“总的来说,哈贝里希的证词与维塞尔的叙述是一致的,只是在一个较小的细节上有所不同。 但这是无关紧要的分歧,不会改变悬而未决故事的实质。 然而,真正影响它的是Wiesel所定罪的年龄之一。 被判刑的年龄是问题的症结所在。
“在最初的意第绪语《热切维兹语》中,以及法文和英文译本中,被谴责的三个中的一个经常被称为儿童或男孩。 Halbereich对受谴责者的年龄保持沉默,这种疏忽令人惊讶。 在维塞尔(Wiesel)对绞刑的详尽描述中,小男孩的死刑激起了站在唱名囚犯中的囚犯的深情。 被指派管理绞刑的卡波免除了自己成为绞刑员的责任。 他不想吊死孩子。 卡波拒绝服从党卫军命令无异于判处死刑。 他的非凡举止一定会在Halbereich身上得到证实,他的证词非常详尽。 Halbereich对Kappo勇气的沉默让Wiesel对吊死的说法产生了疑问。 怀疑论者之一是著名的大屠杀学者劳尔·希尔伯格(Raul Hilberg),用他自己的话说,他是寻求真理的人。
“由于气质和学术纪律,希尔伯格小心翼翼地提出了与上吊场景有关的问题。 在为《波士顿环球报》撰写的关于威塞尔自传体《所有河流奔向大海》的评论中,希尔伯格提到了三处绞刑。 “在他(威塞尔)的《夜》一书中描述了这一事件,”希尔伯格指出,“他回忆起身后有人问:上帝在哪里? 在那一刻,威塞尔相信三个人中的一个是男孩,并在他的脑海中将孩子视为上帝。 引用 Kazin 的论点,即整个事件都是虚构的,希尔伯格得出结论,'当然,怀疑者可能会声称让步。'”
Pfefferkorn 深思熟虑的判断对 Wiesel 对《夜之生命》的绝对真理的主张很苛刻:
“如果悬而未决的场景与威塞尔在他所谓的回忆录之夜中的描述相反,这是卡津声称并从哈尔贝雷希的证词中推测的虚构情节,那么威塞尔的整个道德和神学大厦就会倒塌,随之而来的是“受苦的仆人”神学。首先是对他的认可,并最终使他成名。
“虽然几乎不可能核实死者的确切年龄,但必须指出,正如希尔伯格所观察到的,在威塞尔最近的自传中,‘受苦的身体不再是男孩的身体了。’”
除了神学问题外,场景的部分影响源于维塞尔对这个男孩的描述,这个男孩的体重实在是太小了,以至于绞索无法迅速勒死他。 在最后的分析中,这真的重要吗? 如果您不愿将弗雷与维塞尔的“将记忆作为一种神圣的行为”进行对比,那就可以了。 都是一样,我不认为吸烟枪会高兴地以第三位受害者的出生证明为特征。
在与伊莱·帕弗科恩(Eli Pfferkorn)交谈并阅读回忆录中的章节之后,我给现年80岁的劳尔·希尔伯格(Raul Hilberg)打电话给他在佛蒙特州伯灵顿的家。
希尔伯格开始说:“从纯粹的学术观点来看,有一个学术版本,将意第绪语版本与随后的翻译和版本进行比较,并附上适当的脚注,维瑟尔的评论等,这是很有趣的。他正在针对两个截然不同的听众,第一个是是讲意第绪语的犹太人,他在XNUMX世纪曾谈到的他的青年时代的世界成员。 有更多细节,更多评论。 我向维塞尔提出了这个建议,但他的反应并不理想。”
希尔伯格转向关键场景:“我有一个老幸存者的版本,上面挂着三个成年人的名字。” 那个幸存者曾说过,三人中没有男孩。 希尔伯格在对《夜》的评论中提到了这一点,他在评论中告诉我,“我毫不掩饰我们之间的分歧。 但是,虽然它(被绞死的中心人物的年龄)可能看起来有点小,但它对基督徒,尤其是天主教徒产生了很大的不同,因为很明显,神秘主义者对这一场景非常感兴趣,因为它似乎复制了被钉十字架. 它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 因此,这个数字可能根本不是男孩这一事实令人不安。”
希尔伯格接着说:“根据我的记录,似乎会出现一些目击者质疑这一幕是否发生过的情况。” 我有一位年长的男子作了很长的发言,我认为他是一个值得信赖的人,尽管必须始终记住,有时会在以后观察或听到一些事情。 我最近与营地那部分的幸存者进行了交谈,他说[三人吊死]没有发生,但也许发生得更早了。 我不知道。 幸存者很难约会这些东西。 有人怀疑这会发生。 布纳(Buna)是一个工作营,所以另一个幸存者,历史学博士,非常有才智的人不相信这一点。 我对他说:“你怎么知道这没有发生?” 我认为这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合理的。 但是年龄对某些人来说是个大问题。 这是他在新版书中没有讨论的内容。”
希尔伯格评论说:“威瑟酒是奥斯威辛所有回忆录中读得最多的,不仅因为它的简洁,而且因为它具有神秘,超现实主义的特征。” 他提到小男孩拉小提琴的一集,并说这是如何唤起俄罗斯犹太神秘画家夏加尔(Chagall)的影像的,该画家也是屋顶上的提琴手(Fiddler on the Roof)。
Wiesel来自罗马尼亚的Sighet。 在锡吉特(Sighet)有许多宗教犹太人,也有乌克兰人。 Wiesel成长时,Sighet的许多人都相当原始。 大多数道路没有铺好。 那是生活。 然而,一群同化的犹太人正在涌现。 11年1937岁时,我去了那里,度过了整个夏天。 有一个网球场,非常中产阶级。 我的姑姑和她的丈夫Sigheti在Sighet生产小提琴,那里是小提琴的主要传统。 我在我们的花园里听到了四重奏。 威塞尔的父母有一家商店。 因此,在某些方面,锡耶特(Sighet)处于XNUMX世纪,而在另一些方面,则出现了一群进入XNUMX世纪的犹太人的所有记号,这些犹太人显然对现代文明十分了解。 那么小提琴的场景是现实的,还是幻想? 当然,对于犹太人而言,小提琴是首选的乐器。 它是便携式的。
“所以我不会说小提琴的场面是不可能的,尽管我认识一个来自死亡游行的人,说那是完全不可能的。 他当时也在威塞尔(Wiesel)的年龄,奥斯威辛集中营。 但这仍然并不意味着它没有发生。 没有什么是不可想象的。
“所有幸存者账户的模型都是田园诗般的童年,然后是大屠杀的地狱,然后因为他们幸存下来,他们强调了他们幸存下来的事实。 与威塞尔一起,他的原标题是“世界是寂静的”。 这是指责。 夜晚更加超现实和神秘。 它可以追溯到中世纪。 Wiesel 正好适合这种风格。 这不是小说,但它确实有一个人的烙印,他想留下这样的印象:如果你不在那里,你不知道它是什么样子,但那样就注定了要写出它是什么样子。 ”
我问希尔伯格他最欣赏死亡集中营和大屠杀的哪些记载。 “这真的取决于读者。 我没有那种喜欢的。 就我的目的而言,显然它们必须是正确的。 菲利普·穆勒 (Filip Mueller) 曾在 1942 年与奥斯威辛集中营的毒气室细节有关,他与以下两个人合作撰写:目击者奥斯威辛集中营。 它必须仔细阅读。 另一本书是鲁道夫·弗巴 (Rudolf Vrba) 的《我无法原谅》,与艾伦·贝斯蒂克 (Alan Bestic) 合着。 弗尔巴从奥斯威辛集中营逃脱。 他成为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的药理学教授。 这是最了不起的幸存者,一个绝对令人难以置信的能量和能力的人。 就处理这种情况的纯粹能力而言,这个人是令人难以置信的。”
我没有强调这一点,但向我强调他钦佩威塞尔的希尔伯格并没有将夜列入这个小名单。 这一遗漏的线索可以在希尔伯格 1996 年出版的经常辛辣的回忆录《记忆的政治》中找到。 在“可疑的做法”一章中,希尔伯格以对汉娜·阿伦特的不正当行为的毁灭性描述而著称,他讨论了“不恰当或不恰当的领域”。非法”。 “当诗人或小说家挺身而出他们的艺术时,我尽量明智地点点头,因为他们的艺术本质上比我的要少得多。 当历史普及者挖掘脚注作者的专着(希尔伯格也包括在其中)并提炼内容,为广大读者突出故事和戏剧时,我也不会感到不安。然而,这是有限制的。 让我感到不适的做法之一是创造一个故事,为了情节和冒险,故意改变历史事实。”
希尔伯格随后继续说:“如果反事实的故事足够频繁,那么媚俗就真的很猖The。 我到处都是老生常谈,陈词滥调和陈词滥调。这是德国第一本少量发行的书籍,其中载有我的介绍和有关铁路的文件[viz。 他说,他为此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写了一首诗,描述了货车上的人,包括眼睛闪闪发光的孩子。 对历史的操纵是一种破坏,媚俗是对人的侮辱。”
读到这些台词时,我的脑海里确实立刻想起了《夜朱利克》中在死亡行军中拉小提琴的一些场景,例如,这些场景悬停在媚俗的边缘,或者,为了不那么宽容,投入其中。
“1981 年”,Pfefferkorn 回忆道,“Wiesel 邀请我给他在波士顿大学的研修班学生做演讲。 在我的演讲过程中,我讨论了一些文学作品中记忆和想象的关系。 然后我指出了他在《夜》中使用的文学手段,我强调说,这些手段使回忆录成为引人入胜的读物。 威塞尔对我的评论的反应如闪电般迅速。 在此之前或之后,我从未见过他生气。 在时任波士顿大学校长约翰·西尔伯 (John Silber) 和我邀请的布朗大学学生面前,他失去了镇静,猛烈抨击我敢于质疑回忆录的真实性。 在威塞尔的眼中,就像在他的门徒眼中一样,夜呈现出一种神圣不可侵犯的地位,其重要性仅次于在山上赠送托拉。 西奈。 就真实性而言,这是一部真实记录的作品,几乎符合利奥波德·冯·兰克 (Leopold von Ranke) 的历史记载基准:Wie es eigentlich gewessen,真实情况。”
当他在奥普拉和文学世界的滥用中栖息在他的黄金堆上时,弗雷可以安慰自己,认为制作 Night 并不是“真正的样子”,尽管威塞尔与他的作品之间存在巨大鸿沟实际上忍受了弗雷对自己生活的谎言,在创作文学时,他和威塞尔都从事艺术和情感操纵,将小说伪装成真相。
正如Pfefferkorn所强调的那样,仅仅靠运气,您就无法在死亡集中营中生存。 “例如,在理想的劳动细节中确保位置涉及将生产线推到生产线的顶端,这被认为是值得冒的风险。” 然而,在遇到反对者时,人们不得不知道什么时候该撤退到集中营的变色龙-睡衣般的背景中。 排队喝汤也是如此。 在生产线上找到合适的位置可能意味着要加一碗更浓的汤-这可能会增加一个星期的寿命,但这需要粗暴的弯腰和时间。”
Pfefferkorn 现在说,他一生中最大的失望之一是 Wiesel 对幸存者的“背叛”Pfefferkorn 的话。 纵观这个人的整个职业生涯,我想说,作为一个道德寓言家,威塞尔要回答的远不止弗雷。 奥普拉不应该问他,他本可以帮助数百万人获得诺贝尔和平奖所获得的道德地位,他用粗鲁的肘部坚持不懈地竞选,但由于卑鄙的政治算计而背叛了谁?
尽管诺贝尔委员会称赞他是“人类的使者”,但很难找到维塞尔代表美国政策受害者发送信息的例子,而对以色列受害者来说几乎是不可能的。
在 19 年 1982 月 1985 日接受《全国犹太邮报和意见》采访时,威塞尔的懦弱得到了很好的体现。当被问及在 Sabra 和 Shatila 屠杀巴勒斯坦人时,他说他感到“悲伤”。 为了避免任何人得出结论,威塞尔终于为以色列入侵的受害者表达了悲伤——他在贝鲁特轰炸期间一直保持沉默——威塞尔补充说,这种悲伤“与以色列有关,而不是针对以色列”。 正如他所说,“毕竟,以色列士兵没有杀人”。 XNUMX 年,国土报的一名记者向威塞尔询问了以色列对危地马拉军政府的援助。 作为回应,威塞尔说他收到了一封诺贝尔奖获得者的来信(麻省理工学院的萨尔瓦多·卢里亚(Salvador Luria)在一个月前就这个问题写信给他)记录了以色列对危地马拉大屠杀的贡献,并敦促威塞尔私下采取行动向以色列施压。 《国土报》记者写道,威塞尔“叹了口气”,并说:“我通常会立即回答,但我能回答他什么呢?”
我想维塞尔可以辩称,叹息构成了技术上的沉默,但是为什么他没有走得更远呢?
在《反沉默》第二卷发表的一次采访中,威塞尔说,作为一名散居海外的犹太人,“我选择为不在以色列生活而付出的代价。 . . 不是从境外批评以色列。” 在 10 年 1982 月 XNUMX 日发表在《伦敦犹太纪事》上的另一次采访中,他对黎巴嫩入侵期间对以色列的批评感到遗憾,并提出了以下反问:
“尽管在媒体上散布了大量的谎言,是否有必要批评以色列政府? 还是不管贝鲁特人民遭受的苦难,提供以色列无保留的支持都会更好吗? 面对仇恨,我们对以色列的爱应该加深,变得更加全心全意,并且我们对以色列的信仰更加令人信服,更加真实。”
目前尚不清楚维瑟尔有多少次冒险在以色列境内进行批评。 维塞尔本人提到过一种情况,他在这种情况下施加了通常称为安静的压力。
1986 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后,以色列希伯来语媒体对威塞尔的评论比美国印刷的法定敬语更为有力。 例如,在达瓦尔,一位名叫米里帕兹的记者讨论了 1982 年夏天在以色列举行的关于大屠杀和种族灭绝的会议的麻烦进程。 为响应土耳其政府的敦促,以色列外交部要求删除六项内容关于亚美尼亚种族灭绝的议程。 会议组委会的一些人,包括主席以色列查尼教授,拒绝接受这种干预。 但领导会议的威塞尔确实削弱了。 他退出会议,用帕斯的话解释说,“作为犹太人,他不能对以色列政府采取行动”。
在自由主义周刊 Koteret Rashit 中,以色列记者 Tom Segev 写到 Wiesel:
“他总是小心翼翼,不要批评他的国家。 。 。 。 他对领土情况有什么要说的? 当“现在的和平”组织的人要求他批评黎巴嫩战争时,他回避了这一要求。 他从来没有养成认真反对以色列领导人的习惯。 。 。 。 实际上,他为实现自己的美好愿望做了什么? 鲍勃·格尔多夫(Bob Geldof)做得更多。 。 。 。 如果他们将奖金分配给世界上真正的好人,仍然活着的人,在大屠杀时危及生命以拯救犹太人的人,那将是多么美妙的事情。
“谁像他们一样象征着大屠杀的教训?
“谁能像他们一样值得世界的尊重?”
脚注:这篇文章的早期版本刊登在2006年3月的CounterPunch通讯第4/XNUMX期中。

 RSS
RSS